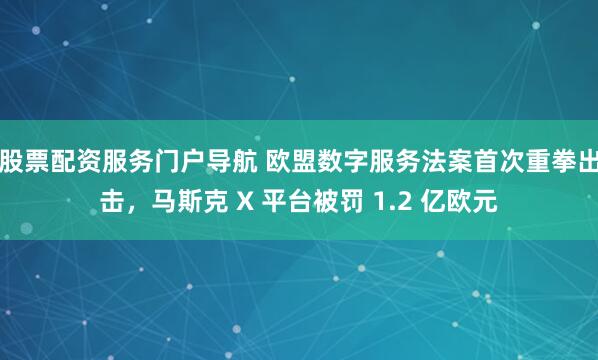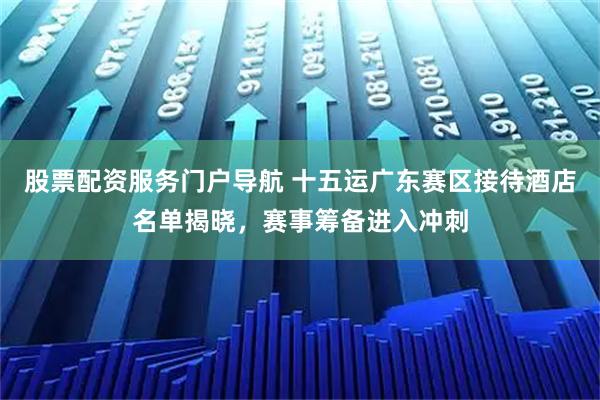连载股票配资服务门户导航
作家薛喜君的长篇小说《沾别拉》近期在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,作品以沾河林业局“守塔人”为原型,生动再现了四代森工人守护山林、转型发展的奋斗历程,是生态文化与文学创作的有益尝试。在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提出20周年之际,我们连载此小说,以飨读者~
作者简介:薛喜君,女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黑龙江省作协签约作家。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,以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见长,出版发行《二月雪》《白月光》等,作品多次获奖。
六
祭祀仪式完毕,刘昌明走到另一棵红松下,用手把树根周围的积雪和腐叶扒开,举起板斧在树根下砍了一个楔子形的碴口。他对伐木工们说:“过去伐根,都在六七十厘米,从这个采伐季开始,以后每一棵伐根,都不得超过十厘米。”
展开剩余95%说完,他沉稳地从姜占林手里接过一把弯把子锯。刺啦刺啦的锯声响了起来。虽然原生林树木茂密,但凛冽的山风依然穿透了树枝,树枝就在风中沙沙作响,伐木工们热气蒸腾的脸又痒又疼。杨石山既紧张又激动,觉得师傅非常厉害,几十米高的大树,在他的锯下像一个俘虏。随着乳黄色的锯末不断溢出,师傅头上的汗也顺着脸颊流下来,滴落到领口处,淌到衣襟上,和冷风相遇,就结成亮晶晶的冰珠子。嘴里哈出来的气,也结了霜。刺啦刺啦——当树根两面的锯口只剩下手指头粗的连接时,师傅站起来。姜占林再次走上前,招呼杨石山,他快步跑上来。
“石山,你推这侧。”姜占林看着师弟,“听我的号子声,使劲推。” “顺山倒,顺山倒啦——”
伐木工们的吼声,打破了雀儿岭的寂静,鸟儿噗噜噜飞起来时,还惊恐地鸣叫。杨石山第一次看到,一棵一抱多粗的红松,在号子声中顺山倒了下去。他感到脚下在颤动。看着倒在山坡下,树枝还在颤动的大树,他激动得差点儿掉下眼泪。他仿佛看到一头黑熊,被师傅制服了。起初,他还为师傅捏了一把汗,这会儿他又为师傅竖起了大拇指。他第一次感受到,无论大树是站着还是倒下,在它面前,人是那么不起眼儿,小得像一棵草。
而大树在师傅面前,又是那么顺溜。
一个多月后,杨石山不但适应了啃冻窝窝头,吃干菜,吃冻成坨的高粱米饭,还学会了烤棉衣裤和鞋袜,也适应了山里刺骨的寒风。他的脸开始皴裂、脱皮,手脚也生了冻疮,裂出一道又一道像小孩嘴似的口子。为了抵挡风寒,伐木工们都不剪头,两个月后,伐木工们个个都像野人。
杨石山能独立伐木了。但刘昌明不放心,给徒弟当了十几天助手,才微笑着把弯把子锯交到他手里。
这个采伐季对杨石山来说,是一次淬炼。大山把他从一个青涩的小伙子锤炼成一个成熟独立的伐木工。姜占林搂着他的肩膀,一本正经地看着他: “男人,是被女人炼出来的;伐木工,是被大山炼出来的。师弟,伐木这一块儿,你成了。”看师弟愣眉愣眼地不知所以,姜占林扑哧笑了:“等明个儿有了女人, 你就知道了;等你当了几年伐木工后,开始带徒弟,你就懂了。”此时,姜占林也开始带徒弟了。
看着师哥神秘的笑,杨石山也跟着笑。
这一冬天,对刘昌明来说就没那么轻松了。工段长既带徒弟,又带队伍。在他心里,每一个伐木工都是妈生爹养的,他把一个个生龙活虎的人带上山,也要把他们囫囵个儿带下山。毕竟伐木不是轻松的活儿,安全最重要。早在上山前,他就喋喋不休地举例子,给新伐木工们讲安全问题。他说大山有神灵,大山恩赐我们很多东西,大山养育了我们,我们就要爱护它、保护它、尊重它——采伐时每一道工序都暗藏危险,特别是原生林的大树,枝杈浓密,作业时穿得又厚,行动自然而然地会受到一些限制,稍不留神就会被枝杈刮倒。轻者只是皮肉受些苦,严重的就有生命危险。伐木前, 一定要判断好方向,伐完要及时避开。若是倒下的大树与周围的树枝缠绕在一起,有的会当即折断,有的则悠荡着悬挂在半空中,这时候就很危险了,因为你无法判断它在啥时候折断,啥时候落下来。遇到这样的情况,一定要冷静,千万不能慌,更不能冒险,或者自作主张地把树钩下来。要先查看周边的地形,再依据风向……除了作业时的危险,还有更大的潜在的凶险,那就是野兽。原生林的老虎、熊瞎子、野猪随处可见。狼和老虎可怕,野猪更可怕。野猪吃人都不吐骨头。
上山后,刘昌明也利用晚上吃饭或者睡觉前的时间,用实例讲安全问题。
他回忆起几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儿。那天,太阳都落下去了,作业的伐木工也陆续收工了。王家驹看天还没黑透,就想再伐一棵,旁边的那棵落叶松也仿佛在召唤他。于是,他再次坐了下来,开始伐树。眼看就要把那棵落叶松锯透了,他忽然听到身后的林子里传来哗啦哗啦的声响,下意识地扭头看,吓得差点儿叫出声。一只老虎朝他走来,他吓得大气都不敢喘,呆愣了好一会儿,才悄悄地起身躲到树后。而那只老虎不知道听到了啥响动,突然跑了。躲在树后的王家驹,吓出一脑门子汗,他怕老虎再返回来,就用手里的弯把子锯猛敲,想通过响声把老虎吓走,把工友们叫回来。
山里的响动,总是让人毛骨悚然,当当的声响没叫回工友,却把老虎叫了回来。老虎张牙舞爪地扑了过来,他再次闪身藏到红松后面……要不是夜色的遮掩,要不是工友赶了过来,说不定他就成了老虎嘴里的食物。王家驹被老虎吓破了胆,从那以后,他不敢独自出门,老是一惊一乍,觉得身后有东西跟着他。晚上,他连撒尿都得有人陪着。
那个采伐季,刘昌明操碎了心,作业时,他总是盯着王家驹,怕他精力不集中,有啥闪失。事儿一忙起来,他就让徒弟跟着王家驹。砍伐季一结束,他就打报告,说王家驹年龄不小了,关节炎还严重。场里经过研究,把王家驹调到了后线工作。
王家驹拱手感谢他:“刘段,俺除了身体,也不只是身体,是精神出了问题,老是一惊一乍,晚上睡觉也不好,白天老是恍惚。”
对于杨石山来说,这个采伐季过得很快。人们打点行李准备下山时,他还咂嘴:“啧,咋这么快就下山了?”尤大勺看着他笑,说:“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,还是嫩,早晚有一天会扛不住,吵着闹着要下山。”杨石山瞥了尤大勺一眼,说:“你不过比我早几年进山,就像个老家贼似的叨叨。”他的话把尤大勺逗乐了,尤大勺眯起眼睛看杨石山,叹了一口气。
“唉,我要不是年轻时逞强,伤了筋骨,腿脚不听使唤,咋能抡大勺做饭?”尤大勺看着他,“你可千万别学我,千万别辜负段长。只有保护好自己,才能在山上多干些年。”
采伐季结束,刘昌明带队下山了。当人马从山上下来,他才从心里轻松了。
七
杨石山直接去了大姐家。
事实上,大姐早就知道他今天下山,从晌午盼到下午,又盼到傍晚。大姐包了萝卜肉馅儿蒸饺,做了小鸡炖蘑菇、粉条,酱炖豆腐。蒸饺刚端上桌,她就看见杨石山从门外进来,差点儿扔掉手里的粗瓷大碗。她哇的一声哭开了,杨石山拉着大姐坐到炕沿上:“哭啥呢,我这不是好好的?”
大姐好不容易止住了哭声,眼泪汪汪地盯着弟弟,他脸上黑一块,白一块,没脱掉的黑皮有的起了壳儿,有的还贴在皮肤上。 一冬天,寒风就给他白净的脸打上了烙印。大姐啜泣着说他壮了。杨石山嘻嘻地笑,说山上挺好,喝着雪水,吃着干菜、咸菜, 啃着冻窝窝头,有时候还能吃顿野味,工段里的人心很齐。看到一根根红松被运下山,他们都特别开心, 一点儿都不觉得苦。晚上睡觉,大伙儿挤在一起,可暖和了。
杨石山瞥了一眼饭桌上冒着热气的蒸饺,咽口唾沫,说:“俺们在山上吃了好几次野鸡肉、狍子肉。手电筒一照,野鸡就把脑袋扎进树棵子里,肥胖的屁股露在外面,还咕咕地叫。”他呵呵地笑起来,“野鸡可真是顾头不顾腚的家伙,一抓一个准儿,一抓就是一窝。狍子肉蘸盐面吃,那是真香啊!”
杨石山眯起眼睛,仿佛又吃了狍子肉。大姐被他逗笑了。姐夫从外面进来,他看一眼姐弟俩,问他们干啥呢,又哭又笑。
大姐斜了姐夫一眼,起身去了外屋。
“石山,陪你姐夫喝点儿,也解解乏,今晚就别回去了,睡这儿。明个儿姐去把家收拾收拾,再烧烧炕,你哪天想回去再回去,不想回就在姐家吃住。”
夏天,伐木工在山下休整。除了林场的工作,伐木工们也都趁着空闲,开荒种地。杨石山在房前屋后种了芥菜、茄子、土豆、辣椒、豆角、西红柿。再上山,吃的用的,就不用让大姐帮忙准备了,他还跟大姐学晒干菜。一夏天,杨石山的脸上黑皮和痂都掉了,手上的老茧不但没软,反而更硬了。他自己也学着做饭,可笨手笨脚,做菜时不是忘了放盐,就是放两次盐,有时候还把没洗的菜放到锅里。贴的饼子,没一次成功,不是出溜到汤水里,就是贴到锅沿上。他对大姐说:“算了算了,我不学了。我手大,只能伐树种地,屋里的活儿我干不了。”大姐笑,说他天生是个爷们儿,这些活儿学不会也没人笑话。
师傅经常叫杨石山去家里吃饭,说他天天来吃饭都行,也不差一双筷子。师娘对他好,只要他去,就变着法做可口的饭菜。师哥也叫他去家里吃饭,嫂子贴的饼子又甜又暄。他也不客气, 一顿吃五六块饼子。师哥的大女儿刚两岁,嫂子的肚子就又大了。每次看到他,嫂子就笑,说:“石山,你要是相中谁家闺女了,嫂子上门去给你说媒。快点儿成个家,哥哥姐姐们岁数都大了,你有着落,他们才放心,也省心。”
姜占林笑着说:“你可真是瞎操心,我看师傅和师娘相中石山了,欣茹也有意思,只是咱们这个师弟有点儿榆木脑袋。”
杨石山嘴里的饼子还没来得及吞咽下去,他半张着嘴看着师哥,若有所思地眨巴两下眼睛,低下头,继续吃喝。
采伐期一到,杨石山又跟着师傅上山了。这次他不但背着粮食、干菜、咸菜、烧酒,还背了两只鸡上山。
刘昌明笑眯眯地看着他,说:“行啊,小子,知道过日子了。你可别把鸡养得剩一把骨头。山上的大雪天,人吃得都不咋样,鸡吃啥?”杨石山嘻嘻地笑,把师傅的行李拿下来,放在自己的肩头,说:“让鸡自个儿刨食吃。不管咋的, 鸡有油水。实在没啥吃的, 鸡骨架也能解馋。要是谁生病了,熬个鸡汤喝也不错。”杨石山还带个手电筒,他想好了,没事儿照只野鸡啥的,吃肉喝汤。尤其是师傅,都五十岁的人了,要是能吃好点儿,师娘也放心。
杨石山怎么也没想到,这个冬天爬上雀儿岭的刘昌明,像一棵树一样倒了下来。
这个采伐期一开始就有些诡异,采伐了二十多天后,姜占林就遇上一件怪事儿。那天,锯透的一棵大黑松,却说啥都不倒下。
“顺山倒,顺山倒啦——”的号子喊了又喊,杨石山和几个人还上去推,这棵大黑松就是纹丝不动。
刘昌明的脸唰地变了颜色,他呵斥住徒弟,还让在场的人疏散。但姜占林和杨石山说啥都不走,他俩一左一右,执拗地站在师傅身边。刘昌明急得眼睛都红了,不敢大声说话,仿佛说话声都能让这棵大黑松突然倒下去。他上前查看,两个徒弟也紧随其后。他相信姜占林,姜占林是他亲手带出来的,平时就稳重,还心细,伐木绝不会有差错。
果然,楔子打得够深,倒向也是顺山。这棵黑松目测有三十多米高,树杈上的针叶密实。树冠呈伞形,枝干横展开阔,雨水都很难穿透它,枝干层层叠叠。刘昌明喜欢黑松,黑松挺拔向上的长相,自带一种气势。但当他看见黑松的树干上有一双像眼睛似的疖子,而且两个疖子长得十分对称,他的心咯噔一下。
“怪事儿,真是怪事儿——”
杨石山的目光又落到这棵黑松上,仔细地打量起它。黑松的树皮呈灰黑色,粗糙且厚,但两个像眼睛似的疖子十分明显。在他的经验里,这是第一次看到黑松上长着这样的疖子,还突兀地鼓出来。 一只乌鸦飞过来,落在树杈上,呱呱地叫了两声后,似乎也预见到了危险,慌张地飞走了。
“呸,丧气的家伙,快滚!”曲二手冲着飞走的乌鸦吐了口唾沫。
远远近近的人都紧张得大气不敢喘,仿佛一口气就能把大树吹倒,只是无法预估它朝着哪个方向倒。
“这是遇上‘坐殿’的树了。”刘昌明让杨石山给他卷一支烟。他接过徒弟递过来的纸烟,用力地吸了两口。 一支烟很快就抽完了,他把烟头啪地甩到地上,又用脚掌把烟头碾进雪里。人们都屏住呼吸,看着他。他摘下帽子,脱掉棉袄,又把棉手闷子甩到雪地里。他吁了一口气,从姜占林手里拿过斧子,目光炯炯地看着两个徒弟,说:“我一会儿给它揳个楔子。听我喊到三,咱们就往东边跑。”他抬了一下下巴,“你俩别回头,跑到那个坡下,蹲下或趴着都行。”
姜占林皱着眉头问:“师傅跑不跑?师傅不跑,俺俩就不跑。要跑就一块儿跑,不跑就都站这儿。”
刘昌明点头:“我和你们一起跑。”
刘昌明找来一块木头,几斧子下去,就砍了一个木楔子。他来到黑松下,照着已经锯断的树根,砸下了木楔子。师傅每一斧子下去,两个徒弟的心都剧烈地颤抖一下。刘昌明的额头上满是汗水,木楔子一点儿一点儿地揳了进去。
“一,二, 三——”
三个人跑到山坡处蹲下来。当他们抬起头时,那棵大黑松依然一动不动,仿佛还在嘲笑他们。
“师傅,干脆咱们把它推倒算了。一棵树还作起妖了,没人了咋的!咱们这么多人,还怕它?我还就不信这个邪——”杨石山被师傅的眼神儿震慑住了,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。
“石山,你带上山的鸡还活着?”刘昌明问。
“还有一只,就是瘦。”
刘昌明让他把鸡拿来,还让姜占林去倒一大碗烧酒,再拿香烛。姜占林和杨石山赶紧去了。
刘昌明双手擎着三炷香,姜占林端着一酒碗,杨石山拎着鸡,师徒三人再一次走到树下。
师傅让他们往后站,他把三炷香插到树根下,把抹了脖子的鸡血淋到树干上的两只“眼睛”上,又把酒贴着树根倒下去。师徒三人跪了下去,师傅嘴里叨咕了几句,然后起身扯着两个徒弟,朝南走去。就在他们走出一段距离后,大黑松顺着北坡倒了下去,发出砰的一声闷响。它倒下来时,把一块裸露的石头砸飞起来。飞起来的碎石块,像一群受伤的小鸟儿,大头冲下地栽下来。
这一声尖利的脆响,把人心震得直颤。
刘昌明看了一眼,徒弟和其他伐木工都好好地站着。凛冽的寒风刺疼了他的眼睛,泪水在他眼里打了一个转儿。
坐殿树让大家唏嘘不已。
“真是撞见鬼了,多少年没遇到这事儿了。按说那个木楔子揳进去,树就应该倒下去了。可这棵大树嘴馋,想喝酒,还想吃鸡。”曲二手嘀咕着,递给每人一支卷烟。
“来,抽支烟,压压惊。来,抽一支。”曲二手还划火帮人点着烟。
人们一边抽烟,一边叽叽喳喳地议论,说今天要是没有刘段,说不定会发生啥事儿。徒弟们面面相觑,他们又将目光投向师傅。朔风穿透密实的松针,身上的汗散了下去。他们拍打拍打手闷子上的雪粒,强迫自己走出坐殿树的阴影,又开始了日常作业。
差不多半个月后,又发生了一场事故。这次,刘昌明没能逃过劫难。
事故发生的前两天,下了一场大雪。雪后,出奇地冷,北风夹着雪花在棉帐篷的檐下号叫了一夜。早上,出工的人推开门时,大风呜的一声吹进来,把人吹得直趔趄。刘昌明系紧棉袄扣,走了出来,杨石山往回推他:“师傅,今儿太冷,你别去了,有大师哥带我们就行。”此时的姜占林已经是伐木段的副段长了。这些日子,刘昌明膝盖疼,残留弹片的小腿也疼得不得了,晚上收工后,都要坐在炉子前,烤一会儿腿,才能上铺睡觉。工友和徒弟都不让他伐树,说他指挥就行。
刘昌明扭过头,躲避着嗷嗷号叫的风,说:“不行,这样的天,我在屋里哪能坐得住。”
到了施业区,刘昌明让大家先清理积雪,他再次强调,保证在树根的十厘米处下锯。这场大雪,增添了伐木的工作量和难度,但工友们都听刘昌明的。他们知道,雀儿岭的每一棵树,都有几百上千年的树龄,它们虽然是树,但论树龄,都是他们爷爷的辈分、祖爷爷的辈分。
大风把雪粒子吹起来,伐木工不停地“呸呸”吐出嘴里的雪粒子。人人身上都披着一层雪,像是长了白色的绒毛。杨石山伐的是一棵一抱多粗的红松,树倒下时,却突然变了风向。大树像是被弹回的皮球,悠然地朝着他的方向砸下来。刘昌明几步冲上去,把徒弟推了出去,他倒下了。
看着倒下去的刘昌明,人们都傻了。姜占林和杨石山号叫着扑上去。“师傅,师傅——”杨石山的嗓子都喊破了。
刘昌明哼了一声,努力地想睁眼睛,眼皮动了两下,就再也不动了。他躲过了坐殿树,却在“回头棒”下丢了性命。
刘昌明下葬,闵学范亲自为他扶灵。他说:“昌明死在伐木场上,与牺牲在战场上一样,都是为了国家……”闵学范哽咽了,泪水从他消瘦硬朗的脸颊上流下来。
师傅永远地安息在雀儿岭上了。
杨石山跪在师娘面前哭,师娘抹了一把眼泪:“石山,别说是你,就是工段里其他人,你师傅也一样会顶上去。”
杨石山满脸泪水——很多年,他都没走出师傅离去的阴霾。
姜占林接替了刘昌明,担任砍伐队队长。
八
秋天来临前,在姜占林的操持下,杨石山迎娶了师傅的大女儿刘欣茹。
婚后第二年,刘欣茹生下大女儿杨春洛。春洛五岁时,她又生了二女儿杨夏璎。她天生瘦弱,生了两个女儿后,身子像是被掏空的鸟巢,几年都没怀孕。没给杨石山生儿子,没给杨家生出一个接户口本的儿子,她无法释怀。看她总是闷闷不乐,杨石山就轻声劝她,说不生了,两个女儿就挺好。刘欣茹噘嘴生气,说:“那怎么能行,镇上的女人谁不生三五个,我倒好,生孩子比下个龙蛋还难,咋对得起祖宗。要是我爸还在,他都不能答应。我爸最常说的是,过日子就是过孩子,孩子越多越好。你还老这么说,咱俩都有信心才行。”刘欣茹说到师傅,杨石山的心一疼,他就不再说话了。
五年后,刘欣茹怀孕了。她抚摸着日渐隆起的肚皮,期盼肚子里装的是个儿子。
“五一”劳动节,杨石山被评为“生产能手”。他登台披红戴花,接受表彰。已经升任木沟壑林场场长的姜占林,带人敲锣打鼓地把杨石山送回家,儿子正好被接生婆剪断脐带。与母体分离的杨思乐,哭声响亮得像个小喇叭。儿子紧赶慢赶,参与并见证了杨石山的辉煌时刻。
“石山,快进屋给儿子起个名吧。”
已经做了春洛和夏璎爸爸的杨石山,在儿子面前,显得有些手足无措。他脸色微微泛红,憋了好一会儿,才说:“就叫杨生产吧。”刚生完孩子的刘欣茹,头发湿漉漉地粘在头皮上,苍白的脸,因为丈夫获得的荣誉,而涌上一片潮红。她对儿子的名字不置可否。看着人们陆续走出院子,刘欣茹才乜斜杨石山一眼,说他高兴得昏了头,生产还能做人名?
刚生了孩子的刘欣茹,因为说话的口气急,虚弱得有些气喘。
杨石山涎着脸嘻嘻地笑:“那你说,叫啥名字?刚才师哥让我给儿子起名,我要是起不出来,工友们都看着我,我下不来台,就顺嘴说一个。”他讨好地看着女人。
“你要这么说,我就不怪你了。重起,这个名儿,实在不好听,太难听了。”
儿子的到来,满足了刘欣茹为杨家生儿子的心愿。卸下了包袱,她心情大好,饱饱地睡上了一觉。早上醒来,她盯着杨石山问:“儿子的名,你想好了吗?你要是还没想好,我昨晚想了一宿,儿子大名叫杨思乐,小名叫树根。他上头有两个姐,两个姐把他锁得牢牢实实,他就能像树一样,从此扎根,开枝散叶。我在家里是老大,我护弟弟的心情,就像护着自个儿的命。姐姐对弟弟,就像妈对儿子。”刘欣茹看着杨石山说,“这个名字可能不随你心,那也比你那个杨生产好听多了。再说,树根这个名儿,虽然听上去不贵气,但贱名好养活,我相信咱儿子一定像虎羔子一样壮实,像大树一样枝繁叶茂。”
“行啊,还会用枝繁叶茂了。”杨石山看着被三个孩子和家事拖累得憔悴不堪的女人点头,“儿子这名儿好听,随心,可随心了。你是妈,妈是孩子们的根,名字啥的,你说了算。”他去外屋端了一碗红糖水,“喝了。孩子是你怀胎十月拼着性命生出来的,我都听你的。”
杨石山说的是心里话。他内心很愧疚,师傅当年把闺女给他,是对他的信任。可他这个丈夫, 一半给了林场, 一半给了木头。对这个家来说,他没出多少力,都是欣茹里外张罗。在这个家,他没有当家做主的份儿,平时他还心粗,很多时候都猜不出欣茹的心思。
“明个儿去落户口,大名就叫杨思乐,小名叫树根。”杨石山拍了一下脑门,笑了,“哦,对了,户口上不用写小名。”
刘欣茹嗔怪地撇了一下嘴:“你少气我,少喝点儿酒,就啥都有了。”她看着男人说,“从现在开始,你不把我供起来,也得给我吃香的、喝辣的。
要不是我,你哪来的闺女,现在又有了儿子。你看咱这两个闺女,水葱一般,谁见谁夸。”可能是话说得急了,她气喘得咳嗽起来。咳嗽好不容易平息下 来,她又安排杨石山:“抽工夫去给爹妈上坟,烧两捆纸钱,告诉爹妈,他 们有孙子了。再上雀儿岭, 给咱爸也捎个信,告诉他,我给杨家生儿子了。”
刘欣茹仿佛又想起啥,沉吟了一下:“嗯,哥哥们也给爹妈生了孙子,但咱家树根,是咱妈的第一个孙子。”
杨石山笑了,眼角的皱纹堆积起来。
刘欣茹能干,过日子也仔细。
一到开春,她就把房前屋后的地开出来,种上一些小菜,一夏天的菜就不用买了。若是赶上秋天雨水充沛,土豆、白菜、萝卜收上来,储存到菜窖里,再腌一大缸酸菜,一冬天的菜也够了。下点儿力气种菜,省下买菜的钱,除了给孩子们添置衣裳,隔三岔五,还能捡两块佟豆腐家的豆腐。酱拌小葱豆腐,换换口味,有时候也炖豆腐汤,就着苞米面饼子,孩子们都爱吃。
刘欣茹还养猪养鸡鸭,两年杀一头猪。㸆猪油,连油带渣存放到坛子里,隔三岔五挖一勺子,夏天炖茄子豆角,冬天炖酸菜粉条,给孩子们解馋。无论日子多艰难,她都给杨石山留下一坛子荤油。她对大女儿说:“你爸不容易,小时候能活下来,就是命大。生他时,你爷都六十来岁了,你爷一辈子都在山里做林工,不是伐木,就是拉套子。据说你爷还放过排,他的身手好得不得了……你爸刚出生,你爷就剩下半截身子,落炕了,你奶伺候你爷,哪有心思管你爸。听说你爸是喝米汤长大的,要不是你的三个姑,你爸兴许都活不下来。从小亏空的孩子,后天不好养。你爸干的是林业局最累最苦的活儿,又冷又危险,你姥爷看好你爸,就是因为你爸能干,能吃苦,品行还好。你姥爷把你爸当儿子,为你爸,也为我。这个世上,只有爹妈能为儿女豁出命。你爸也记挂着你姥爷,你姥爷活着时,你爸有一口好吃的,都给你姥爷留着。你姥爷没了,逢年过节,不等我说,你爸一定去雀儿岭看他。平时工作遇到点儿啥事儿,他就是不和我说,都要去你姥爷的坟头上说说;对你姥更没的说,你姥爱吃炉果和槽子糕,咱家的日子再紧,他宁可不抽烟,少喝一顿酒,都买给你姥……大冬天,你爸就带着几十上百号人上山伐木,肚子里没点儿油星哪能行?哪怕吃窝头,能吃一块荤油,抗饿还抗冻……”
一说起杨石山,刘欣茹就滔滔不绝,眼眶盈满泪水。她从心里觉得男人可怜。
多了一个孩子,就多了一张嘴,刘欣茹要去到林场的育苗圃干活儿。她躺在炕上,柔声细语地说服杨石山:“全家人的柴米油盐,都靠你那几十元工资。虽然你的工资比别人多出十几元,但那是你拿命换来的。”每个采伐季,杨石山这个队都会被派往最高最原生的施业区,高寒地带,每月有十九元高寒补助费。
“每月我一拿到工资,心里可不好受了,我要是能再挣两个,就能减轻你的压力,还能让孩子们吃得好一点儿,穿得好一点儿。哪怕能给孩子们买点儿零嘴吃,也是好的。春洛从小就懂事儿,自从弟弟出生,她就能干一些简单的家务,也能带妹妹和弟弟。你明天就去给我说一声,我去苗圃干活儿。”
杨石山“嗯”了一声,说:“明个儿我去说一声,你也别抱太大希望,万一苗圃不缺人。”
“缺人。你要是不说,明个儿我自己去找大师哥。”
“行,我去,我去——”师傅为他丢了性命,扔下一大家子。刘欣茹又为他生儿育女,自从和他结婚就没消停,除了生孩子,照顾家,还要照顾有严重风湿病的师娘和弟弟妹妹。这几年,弟妹们陆续工作、成家, 一家人的生活才有了改善。弟弟把师娘接到县里住了。欣茹得空才能去县里,给师娘送一串干蘑菇、一篮子鸡蛋。自从嫁给他,她没享过福。杨石山很感激女人,但他不善于表达。只有喝了烧酒,他才拥着女人干瘦的身子,说让她受苦了,等日子好了……
刘欣茹不等他说完,就责备他,说他又被烧酒烧昏了脑袋瓜,开始胡说八道。她说一天有吃有喝,三个孩子围前围后,还有个能干的男人, 一点儿都不苦。
“你看看,就拿龙镇来说,咱家的日子比谁家差吗?咱家养的猪,比他们的都肥,咱家的鸡也能下蛋,你一天能喝一碗鸡蛋水,隔三岔五,孩子们也能吃个煮鸡蛋。不光猪、鸡、鸭养得好,孩子也听话。咱家春洛将来不是大学生,就是当干部,说实在的,我可知足了。”
刘欣茹仿佛吃了啥香东西,说话时不停地咂嘴。
“睡觉吧。你得养好身子骨,要不你干不了苗圃里的活儿。”杨石山咕哝着。
(未完待续)
来 源:龙江森工
责 编:卢秋影股票配资服务门户导航
发布于:北京市永旺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